摘录和改编,得到约旦萨拉玛的许可河流每天都在变化:马格达莱纳河下游的四周,由Catapult Books出版社于2021年11月出版。版权所有©2021 by Jordan Salama。
路易斯·索里亚诺生来如此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每个人都确信他会死,这还为时过早。
1972年,他出生在哥伦比亚拉格洛里亚(马格达莱纳省)的同一个村庄,在那里他长大并开始了他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场主,他的母亲在路边卖水果和牛奶。他们很勤劳农夫父母向他们的许多孩子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超过一切。
路易斯在马格达莱纳山谷起伏的田野里玩耍长大。拉格洛里亚位于河的内陆,距离河大约一个小时,但这条河对小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它是在河运的黄金时代建造的,当时前往蒙普拉和柏拉图等河运港口的旅行者不可避免地会在拉格洛里亚停留,以便继续运输,当时农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船只,将他们的产品运输到哥伦比亚的另一边。在镇上,据说马格达莱纳河决定了附近低地的降雨和洪水,这影响了拉格洛里亚的降雨和洪水,在干旱期间,该镇感受到了河流的痛苦。这条河的海滩和多沙的岛屿上生长着丝兰、大蕉和加勒比海饮食中的豆类——拉格洛里亚距离最近的加勒比海滨城镇近100英里,但是的,它的人民会告诉你,它确实是一个加勒比地方。

路易斯在农村长大,他从农村学到的东西是城里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在炎热潮湿的下午,一排蚂蚁匆匆走过小路,这意味着天空即将开阔,大雨将倾盆而下,清新空气;到了晚上,青蛙和蟾蜍突然沉默了,这意味着黑暗中有另一个人正在靠近。通过观察这些鸟,他收集了一些关于它们日常生活的观察结果,比如红绿相间的金刚鹦鹉喜欢在哪些树上过夜,sirirí在一天的什么时候唱它孤独的歌。这些都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的,并伴随他一生。
但是哥伦比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升级的暴力意味着路易斯无法留下来。当准军事部队和其他犯罪集团肆虐拉格洛里亚和周围的乡村时,路易斯的父母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送到了几小时车程外的瓦列杜帕尔。他在动物中玩耍的生活被一个山谷城市嘈杂、粗糙的街道所取代。
当路易斯高中毕业回到La Gloria的时候,他决定,也许是他自己生活中学习和吸收的结果,他想成为一名教师。他在新格拉纳达附近的一所小型农村小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教阅读和写作。与此同时,他完成了马格达莱纳大学的远程学位。
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的学生都没有做任何功课,似乎也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路易斯为此责怪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老师,他错误地判断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一切都是因为学生们似乎没有在学习。他意识到,许多孩子住在离最近的学校有几英里远的狭窄的土路上的农场里,因为没有书籍,他们无法在家练习阅读。作为一名资源有限的教师,他决定做一件他唯一能做的事:把自己的书带给他们。
就这样,1997年的一天,天还没亮,他就牵着一头驴,带着一堆书,横穿乡村。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好几英里,在每个学生家里都停下来和他们一起阅读,然后把书借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他第二天会来取书。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在清晨,早在学校开始上课之前就回来了,因为他从经验中知道,住在田野里的家庭是在sirirí的第一声歌声和黑暗中公鸡的叫声中起床的。
20多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停止。路易斯喜欢说:“起初,人们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半疯的老师,带着一些书和他的驴。”“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创建了这个乡村旅行图书馆,就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Biblioburro。”
Biblioburro一开始只有70本书,都是路易斯自己的,还有一头驴。为了方便运输,他很快又添了一头驴,并在它们的马鞍上绑上了木制书柜,并给这两头驴起名为阿尔法和贝托。alfabeto,西班牙语字母)。他开始扩大每天的路线,使其多样化,以帮助该地区更多的儿童。当受人爱戴的哥伦比亚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Juan Gossaín在2003年听到了Biblioburro的故事,并与听众分享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捐赠开始涌入——今天,Luis拥有7000多本书。

然而,尽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它仍然是一项不起眼的行动。当路易斯出发去参观图书馆时,他独自一人,安静地带着他的两头信任的驴子。通常情况下,他在崎岖、孤独的地形上穿行时,几个小时都不会遇到其他人——在无情的阳光下,这是一段不舒服的旅程,更是一段更艰苦的行走。但是,生活在这些偏僻地方的孩子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等待着藏书馆和里面的故事的到来,当他们Beplay客户端安卓版在地平线上发现阿尔法和贝托时,他们会睁大眼睛朝它们跑去。
也许,在他服务的孩子们身上,路易斯·索里亚诺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他认为他们可以克服困难,因为尽管路易斯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拉格洛里亚最著名的人,但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你很难找到任何人想象他会像他一样从困境中恢复过来。
只有一个人例外。据说,他的父母请了一位在镇上很受尊敬的老妇人来检查孩子,并为他祝福。路易斯出生几分钟后,她走到家里,站在他身边,上下打量着他小小的身体,似乎在思考他是否注定会和她一样长寿。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这个小家伙,他不会死的”是老妇人说的(谁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句话)。“他长大后会成为一名医生,他会拯救这个小镇。”
那天早上我们出发晚了,因为路易斯·索里亚诺的摩托车坏了,他得找一个替换零件。我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趴在他那辆旧雅马哈(Yamaha)上,就在一个朋友的汽车修理厂外面。实际上,这家修理厂不过是一个住着几只猫和一个人的木棚子。
“医生,”几分钟后,那人从他那乱糟糟的棚屋里走出来,路易斯抬起头来。他不是医生,尽管从他少年时代起大家都叫他这个绰号,但他并不以为然。“你都准备好了。”
”谢谢,朋友.”
我注意到路易斯走路有点瘸,他把刚修好的摩托车推到路边,示意我跳上去。拉格洛里亚是一个过境小镇,是一个有两条路的村庄,建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创造了方圆几英里内唯一可以找到的十字路口。他开车带我们拐了30秒,来到一个没有标志的黄色建筑前,对面是一家嘈杂的餐厅和一所更嘈杂的学校。在这个角落里,他不仅被称为“博士”,而且被称为“教授”——这所学校是他创办的一所公立学校。隔壁的餐厅是他妻子的,那里炖菜和炸肉的味道飘过那些在阴凉处喝着冒汗的橙色苏打水的男人身边。路易斯一句话也没说,在家里消失了几分钟。拿着扩音器的男人开着皮卡从这里经过,兜售着一箱箱味道扑鼻的柽柳水果。在离房子、学校和餐馆几英尺远的路上,我注意到树荫下有一幅彩色的壁画,画着一个男人,在两头微笑的驴子的陪伴下,张开双臂向孩子们分发书籍。

几分钟后,壁画上的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个彩色的木箱,里面装满了成堆的儿童图画书。他把每个人都挂在摩托车后座上,然后我们又出发了,沿着最初把我带到La Gloria的那条路往回走。我想知道我们会走多远——在从蒙痘到这里的路上,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除了开阔起伏的牧场中零星的几座农舍,什么也没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了一个叫圣伊莎贝尔(Santa Isabel)的地方,沿着高速公路走了一英里左右的土路岔道。我们来到一间小小的农舍,俯瞰着一些牧场,牧场上有几十头牛。路易斯说,这就是他现在养阿尔法和贝托的地方,因为拉格洛里亚的路边挤满了卡车和汽车,动物们无法安静地吃草。
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路易斯朝农舍喊了一声,一个农场工人走了出来。他带我们去找一匹拴在农舍旁边一棵树上的驴子,茫然地望着天空。
“在哪里拉巴拉路易斯问道,我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贝托。“你能帮我把她叫来吗?”
“嗯,我不知道……”那人渐渐说不下去了。
“只是”——路易斯凑过来压低声音,以免冒犯驴子——“这家伙走得太快了。”
农场工人指着房子后面的牧场。“她在那边,”他说。我看了看,除了灌木丛、几棵树,还有几十头牛静静地吃草,忙着自己的事。看不到驴子。
“啊”。路易斯点了点头。他开始向贝托走去,贝托已经听候我们的差遣了。“她离得太远了,”他说。“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她。我们得自己对付贝托了。”然后他再次警告说:“但是要小心,他走得很快。”
我明白了,点了点头。“没问题,我喜欢走路,我能赶上。”我说。路易斯礼貌地笑了笑。

我错了。与贝托并肩行走可能是人类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不一定是因为他以光速行走,而是因为作为“贝托”而不是“阿尔法”,他习惯于跟随领导者——任何领导者。通常路易斯只带阿尔法,或者阿尔法和贝托都带。但是今天,贝托独自一人,走出了他的舒适区。他不习惯带路,就倾向于跟着某个人,而那个人恰好是我。
路易斯把书柜套在贝托的马鞍上,骑上他,长途跋涉到附近的一些家庭。我只能走在这只动物的正前方,因为它会紧紧跟着我的脚步,在我身上留下印记,就好像我是阿尔法或什么母鹅一样。如果我落在后面或停下来看什么东西,他也会停下来转过身来。如果我想偷偷溜到一旁拍照,他就会转身向我走来——甚至试图跟着我爬上我爬过的山,以获得更高的有利位置。最终,路易斯厌倦了,我想,他下马用绳子牵着贝托,把我从领导职责中解放出来。
看到路易斯走路,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之前注意到的那种轻微的跛行又回来了。我觉得这对他这样一个46岁的人来说很奇怪,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很好,但我没有问。在某个地方,我们来到了一根横过小径中间的大树根前,贝托小心翼翼地跨过了它。“五年前,我和阿尔法和贝托发生了意外,”路易斯对我说。当阿尔法被一根像这样的木头绊倒时,他从上面掉了下来,一只动物踩到了他。“我的右腿裂开了,我的骨头暴露在外,我受到了严重的感染,医生不得不截肢。”在了解他工作的各种基金会的帮助下,他前往乔治亚州和田纳西州进行手术。他微微提起裤腿,给我看一个金属假肢。“我真的不能再那么容易地骑上驴了,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路易斯温柔地讲着这个故事,就像在给孩子读书一样。他说话总是这样。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
就这样,我们继续走在我们的路上,除了散步、聊天和看着这片土地,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当然,哥伦比亚没有真正的冬天,只有雨季和旱季,一切都是绿色的。一群黄色的蝴蝶在路易斯和贝托的前面飞舞,我又一次想起了《百年孤独在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Mauricio Babilonia)到来之前,他总是画着黄色的蝴蝶,这个角色代表着在这个斗争的世界里有爱的一切。路易斯说,这些蝴蝶原产于马格达莱纳省,García Márquez在那里长大;它们柔和的翅膀和路易斯最喜欢的cañaguate树的叶子是一样的黄色。路易斯说:“成为Biblioburro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被周围的自然世界分散注意力。”“我可以告诉你,在最壮观的日子里,我看到过多达300只鸟。你会看到许多不同颜色的蝴蝶,注意昆虫的行为。”

“但动物也会警告你危险,”他补充说。“如果你听到啄木鸟不停地尖叫,那是因为有人藏着,看着你在做什么,或者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在你中间。啄木鸟是一个警报。”
这在那些年前尤其有用,当时准军事部队一直存在,绑架是一个持续的威胁。犯罪集团经常以哥伦比亚各地的教师为目标并杀害他们,他们指责这些教师通过课堂上的左翼教学法在未来的游击队中培育颠覆活动。路易斯是个如此显赫的人物,这也无济于事。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汽车旅行过去只有乘坐大篷车才安全。到处都是士兵,但也有强盗;他们烧毁公共汽车,杀害和折磨牧场主,让拉格洛里亚这样的村庄陷入恐慌。多年前,有一次,路易斯骑马穿过乡村,被小偷绑在树上。他们只偷了他收藏的一本书。
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叫他路易斯的人。博士,教授,图书馆.这是一个有很多名字的人,所有这些名字都被在Berenice家等我们的一大群人轮流抛出Díaz,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大草原步行。
“他们住在没有电的地方,”我们朝房子走去时,路易斯低声对我说。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完全由几根高高的笔直的原木撑起一个棕榈叶屋顶。

贝蕾妮丝Díaz带着一种令人敬畏的母系优雅,坐在塑料椅子的宝座上,主持着他们宽敞的小屋,那是他们的客厅。它的四周完全暴露在外,没有任何墙或挡板来挡风或挡雨(另一间同样大的小屋在更远的地方,前面种着茄子、豆子和玉米;我猜想那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因为它确实有挡板,越来越多的人从里面出来)。十几位家人围坐在她周围,互相聊天。一名男子在吊床上打盹,吊床挂在支撑屋顶的两根圆木之间。一只棕白相间的狗静静地躺在坚硬的泥土地板上,而她正在同时喂奶五只幼狗。贝蕾妮丝的丈夫看上去比她老得多,他给路易斯和我端上了几杯糖(rio tinto)这道菜是用新鲜甘蔗在附近一间厨房小屋里的燃木火炉上烹制的。我啜饮着咖啡,能尝到烟熏的味道。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驴上的旅行图书馆时,我们都笑了,”贝蕾妮丝的一个已成年的儿子说,“直到我们看到他带着一堆书、笔记本和笔沿着马路走来,他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孩子们紧紧跟着他。”
“当Juan Gossaín把他放在电台的新闻里时,我们也笑了,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前排看到了这一切,”贝蕾妮丝补充道。“我说,‘看博士在哪里,他在Bogotá收集书籍,为我们带回来。’”
“这太好了,”我说,“可孩子们在哪儿呢?”
“我去拿,”一个女人说着站了起来。几分钟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另一间小屋后面走了出来。这个女孩抱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名叫Josué。他们跑向贝托,注意到他站在树荫下,在一些树下,等着路易斯跟着。他做到了。
“你想看书吗?”Luis问道。
“如果!这个12岁的女孩热情地回答。这个看起来大约10岁的男孩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路易斯拿出一本书叫La cosa que más世界的决斗(世界上最伤人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受伤,对吧?”路易斯大声问道。孩子们什么也没说。
“从前,有一只鬣狗和一只野兔在同一条河边相遇,于是决定一起去钓鱼。”路易斯用西班牙语念给孩子们听,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钓鱼的时候,兔子问鬣狗:‘你知道世界上最疼的东西是什么吗?”
“大象的跺脚声,”鬣狗回答。
“不!”said the hare.
“牙痛。
“不!”the hare said again.
“‘黄蜂的刺。’
“‘也不是那个!”
“鬣狗玩腻了,说:‘我放弃!”
“世界上最伤人的事是说谎。”兔子回答说。

男孩和女孩都被迷住了——尤其是那个安静的男孩,他的眼睛盯着路易斯,默默地被迷住了。贝托耐心地站在他们身边。
路易斯用舒缓的声音大声朗读,节奏缓慢,几乎像音乐一样,不亚于我曾经遇到的任何一位老师。想到现在有一个由近20个Biblioburro流动图书馆组成的网络,每个图书馆都在马格达莱纳区独立运作,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在做这种事情,我不禁笑了。2000年,在阿尔法和贝托工作了三年之后,路易斯得以开办了拉格洛里亚的第一所小学和永久性公共图书馆,现在这里摆满了电脑和平板电视,还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然后,他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创办了第二所学校,第三所,第四所。Biblioburro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全部门的项目,计划推出两项新举措,Biblioburro Digital(为农村地区的儿童提供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技术)和Biblioburro Very Well(教儿童英语的Biblioburro)。
我们又花了几个小时和贝蕾妮丝和她的家人坐在棕榈叶下。临近午餐时间,又有几个孩子从地里慢慢地走了进来。他们在路易斯周围围成一个圈,路易斯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他又大声朗读了几本书。躺在地板上的狗继续默默地哺育着她的幼崽,灰色的烟继续从木制厨房里滚滚而出。有时,路易斯会鼓励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读书给其他孩子听。一个女孩答应了。在大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中,她读了一页,然后脸红了,把书还给了路易斯。
“这让我很满意,”路易斯后来告诉我。“我的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这让我很高兴。”他的父母,一向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也上了年纪——母亲82岁,父亲86岁。他们看着他们的儿子长大,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挑战了所有对他不利的条件。但路易斯·索里亚诺不是一个只考虑自己的人。他注意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从读书的孩子们,到搬重物的阿尔法和贝托;从sirirí会唱歌的鸟,到García Márquez的黄色蝴蝶,它们让他想起了他最喜欢的cañaguate树上美丽的叶子。
差不多是我们该回去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在路上已经汗流浃背了,太阳在天空中越来越高。我正在和那个刚从吊床上打盹醒来的男人聊天,路易斯收拾完东西抬起头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示意我不要小题大做,然后指给我看那个害羞的男孩,他坐在几英尺开外的一张塑料椅子边上,那把椅子对他来说太大了,就在其他人旁边。这个男孩有一本书叫La莫斯卡(苍蝇),嘴里念叨着几分钟前路易斯还在大声念的台词。“‘伟大的日子到了,’苍蝇说,‘他静静地念着。“‘该洗澡了……’”藏书室的美妙之处——我们在那一刻所见证的——正是多年前路易斯第一次当老师时所缺少的:这个内向的男孩,可能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会发现自己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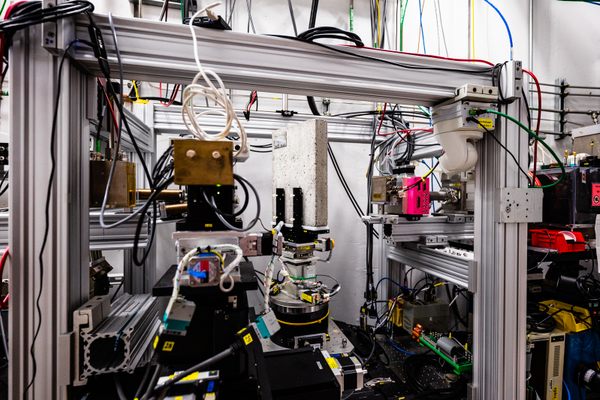














在推特上关注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迹。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了解世界上隐藏的奇迹。
在Twitter上关注我们 在Facebook上喜欢我们